作者:坦途宏观
本文分五个部分,前两部分介绍商品超级周期的定义和数据源,第三部分通过叙事回顾5轮超级周期,第四部分讨论超级周期的五个特征,第五部分展望并总结。
一、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定义与历史研究
大宗商品超级周期(Commodity Supercycle)是指大宗商品真实价格经历的长达数十年(通常为20至70年)的长期趋势性偏离。与通常持续3-5年的短期商业库存周期(Kitchin Cycle)或7-11年的设备投资周期(Juglar Cycle)显著不同,超级周期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时间跨度长。一个完整的周期包含长达10至35年的上升期(Boom)与随后的下降期(Slump),其驱动力源于长期的结构性供需错配而非短期的市场情绪。二是覆盖范围广。Heap (2005) 指出,超级周期的商品价格波动广泛覆盖能源、金属、农产品等基础原材料品类,呈现出高度同步性(Comovement)。
商品超级周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长波理论的思想传统。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在1920年代通过分析1789年至1920年间英、法、美三国的批发物价指数,首次提出了经济存在40至60年长周期的假说。他特别强调,原材料和农产品价格是长波中最为敏感的指标,其波动往往先于并放大整体经济的长期起伏。熊彼特(Schumpeter)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将长波与"创新集群"(Innovation Clusters)联系起来:当基础性技术革新(如蒸汽机、电力、内燃机、信息技术)出现时,会引发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浪潮,从而系统性地拉动资源需求与大宗商品价格。
当然,现代商品超级周期研究与传统康波理论存在重要差异。首先,超级周期的分析聚焦于商品市场本身,强调供给-需求的具体机制。其次,当代研究更依赖于计量经济学工具(如频谱分析、小波分析、HP滤波)来识别和验证周期的存在,而非仅凭价格指数的视觉观察。最后,超级周期研究更加重视特定历史事件的因果机制——例如,第五轮超级周期(2003-2014)明确归因于中国加入WTO后的工业化需求冲击,而非抽象的"长波规律"。因此,尽管两者在时间尺度和价格波动现象上存在相似性,但超级周期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实证数据和结构性解释的商品市场分析框架,而非宏观经济周期的决定论理论。
二、数据介绍与大宗商品指数构建
本文使用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David S. Jacks构建的全球大宗商品长周期价格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42种具有代表性的大宗商品,涵盖四大类别:农产品(包括谷物、热带作物、畜牧产品等)、工业金属(如铜、铝、铅、锌、锡、镍等)、贵金属(黄金、白银)以及能源(煤炭、石油)。这42种商品在2019年的全球年产值约为7.43万亿美元,有较强经济代表性。数据的时间跨度从1850年至2024年,覆盖了工业革命以来175年的长历史周期。本文在原始数据基础上手动补充了2025年的数据。该数据集采用年度频率,且所有价格指标均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作为平减指数,转换为实际价格(Real Prices),使得跨越一个半世纪的价格序列具有可比性。这种处理方式对于识别长期结构性趋势和超级周期至关重要。
在本文中,我们简单将42种商品价格做代数平均作为大宗商品价格的代理指标。之所以不用产量加权,是因为目前大宗商品中能源占比较高(超过50%),使得产量加权生成的指数基本上是能源指数。图1展示了根据简单平均计算得到的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如不特意提及,后文中的大宗商品指数均指通过平均法计算得到的指数。
图1: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平均法)
数据来源:David Jacks、GMF Research
三、1850年以来的5次商品超级周期
结合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与文献,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过去200年人类历史上的5次超级周期。在这一部分中,我们从叙事角度回顾这五轮周期。
1、第一轮(1850-1898) :工业革命全球扩散与美国内战
19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生产模式开始向欧洲大陆及北美地区扩散,全球铁路网的大规模铺设成为这一时期最核心的需求驱动力。Jacks(2013)指出,这一阶段标志着交通技术革新与全球"市场整合"(Market Integration)的开端。铁路和蒸汽船的普及极大地增加了对煤炭、生铁和木材的消耗强度。同时,美国东海岸及西欧地区的快速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建筑材料需求的结构性上升。这一时期的工业化扩张具有明显的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特征,单位工业产出的大宗商品投入系数远高于后续周期。
供给侧,1861-1865年美国内战导致全球棉花供应链断裂,引发了著名的"兰开夏棉花饥荒"(Lancashire Cotton Famine)。由于南方各州棉花出口几乎完全中断,英国兰开夏郡的纺织业陷入停滞,数十万工人失业,棉花价格在1863年达到战前水平的四倍以上。此外,当时的采掘技术仍处于劳动密集型阶段,供给弹性极低(Inelastic Supply)。面对需求的激增,矿山扩产受限于有限的地质勘探能力和落后的开采手段,导致金属价格在高位维持了较长时期(Radetzki, 2006)。这种供给端的结构性约束与需求侧的工业化浪潮相叠加,共同支撑了本轮超级周期的价格上涨。
2、第二轮 (1899-1932) :二次工业革命与一战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集群爆发。电气化对铜的需求、内燃机对石油和铅的消耗、以及化学工业的兴起,共同塑造了新的资源消费模式。美国作为新兴工业强国,其制造业产值在这一时期超越英国,福特制(Fordism)所代表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模式极大地加速了原材料的消耗速度。1910年代的欧洲军备竞赛以及随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将这一需求推向了顶峰。Lewis(1978)和Cuddington & Jerrett(2008)的研究均指出,战争期间的军需生产对钢铁、铜、硝酸盐等战略物资的需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强度。
一战期间,全球航运受阻,跨大西洋贸易成本激增。尽管当时并未出现类似后来OPEC那样的卡特尔组织,但战争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和运输瓶颈,实质上造成了供给侧的瘫痪。这种由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供给刚性,使得价格在战争期间及战后重建初期维持了极高的溢价。
3、第三轮(1933 - 1971):凯恩斯主义、马歇尔计划与欧日工业化
大萧条后的凯恩斯主义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与罗斯福新政开启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复苏进程,但真正的需求爆发源于二战期间"总体战"(Total War)体制对工业产能的极限动员。战后,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 1948-1952)主导下的欧洲重建、冷战初期的全球军备竞赛,导致了恐慌性的大宗商品抢购。Kindleberger(1986)指出,这一时期的需求特征呈现出高度的国家主导性,公共部门支出取代私人投资成为驱动商品超级周期的核心引擎。1950年代至1960年代,欧洲主要工业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日本进入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其制造业扩张对金属、能源的持续需求支撑了长达二十年的商品价格高位运行。
二战导致了欧亚大陆工业与采掘能力的物理性毁灭,全球供应链支离破碎。战后初期,尽管美国产能全开,但其余世界的供给响应能力几乎归零,支撑了1947-1951年的高价格。但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以及“石油七姐妹”(Seven Sisters)对中东能源开发的垄断,供给端在50年代后进入了长期受控状态,有效地压制了名义价格的波动,直到70年代初体系崩溃。
4、第四轮 (1972-2002) :大滞胀、石油危机与美元信用体系重构
宏观和货币政策层面,1971年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脱钩,全球进入了法币信用扩张期。由于央行(尤其是美联储)在初期采取了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s)的宽松政策,试图以更高通胀换取就业,导致通胀预期脱锚。实物资产成为对冲信用货币贬值的首选,金融属性首次在大宗商品定价中占据主导地位 (Frankel, 2008)。
供给侧方面则是一连串地缘冲击引发的石油危机。1973年赎罪日战争引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及1979年伊朗革命引发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展示了供给端的人为垄断(OPEC禁运)如何引发价格的指数级暴涨。Hamilton (1983) 的实证研究表明,油价的剧烈波动直接导致了随后的滞胀(Stagflation)。此时的商品价格上涨并非源于经济繁荣,而是源于供给短缺和货币贬值的双重共振。
5、第五轮 (2003-2020) :中国崛起
中国加入WTO(2001年)释放了巨大的资源需求。与欧美成熟经济体不同,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快速城镇化阶段,其单位GDP的金属消耗强度(Metal Intensity of GDP)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根据 World Bank (2009) 的数据,中国在这一时期消耗了全球约40%-50%的精炼铜、铝和铁矿石。这种单一经济体带来的需求量级,在历史上仅有19世纪末的美国可以比拟。
供给侧,在1980s-1990s的大宗商品熊市期间,全球矿业巨头大幅削减了勘探预算和资本开支(Capex)。当2003年中国需求突然爆发时,全球矿业实际上处于“无矿可采”的窘境。这种产能响应的极度滞后,导致了价格在2003-2008年间,以及2009-2011年间出现了脱离成本曲线的暴涨。直到2012年后,前期巨额投资转化的产能集中释放,才终结了这轮超级周期。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我们将5轮超级周期的高点低点以及不同品类商品的累计涨幅和跌幅统计在表1中。
表1:五轮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统计指标
(GMF Research制表,所有价格指数均为扣除美国CPI通胀后的真实价格)
注:黄金在1898-1920区间内真实价值持续下跌,故视涨幅为0
数据来源:David Jacks,GMF Research
四、商品超级周期的5个特征
1、 大宗商品真实价格指数趋势性下降,且每轮周期峰值往往低于前一轮高点。
图2显示了三种处理方法下商品价格的走势。可见,无论使用均值,还是中位数,抑或改变不同商品真实价格指数的标准化基期,只要我们不采用产量加权(会严重对能源有偏),所得到的商品价格指数在长周期看均呈现趋势下降态势。
这意味着,百年尺度长期单纯持有大宗商品实物,在扣除通胀后难以产生超额收益。这在超长周期上验证了普雷维什-辛格假说(Prebisch-Singer Hypothesis),即初级产品相对于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倾向。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这也可归因于部门间技术进步的差异:采掘业与农业的机械化、自动化技术迭代速度较快,大幅降低了单位生产成本;而作为通胀平减指数(CPI)核心构成的服务业,其技术进步相对缓慢(即鲍莫尔成本病),导致服务业通胀率长期高于原材料通胀率。因此,百年尺度上看,以CPI平减后的商品价格自然呈现出向下的斜率。
数值上看,商品超级周期的平均持续时长约为 33年(含上升与下降期)。其中,上升阶段持续时间大约为 13年,总指数从周期低点到高点的平均涨幅为 75%;下降阶段的持续时间大约为 20年,指数回撤幅度约为 47%。
图2:三种指数处理方法以及趋势线
数据来源:David Jacks、GMF Research
2、商品内部看,不同品种趋势分化
图3和图4展示了工业金属、农产品、黄金和能源四类商品的长期真实价格趋势,可见工业金属和农业品长期下降,贵金属和能源则呈现中枢回归特征。
农产品的真实价格长期下降容易理解。在需求侧,人无论多富裕一天都是三顿饭,因此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天然很低,且食品支出在总消费中的占比也趋势性下降(Radetzki, 2010)。但在供给侧,现代农业经济通过“绿色革命”(化肥、育种、转基因)实现了在有限土地上的单产指数级增长,供给曲线大幅右移(Federico, 2005)。
工业金属方面,开采技术和回收技术的改善抑制价格。尽管高品位矿石在不断耗竭,但Barnett & Morse (1963) 在其经典著作《稀缺与增长》中提出,提取技术的进步(如露天开采、浮选法、溶浸采矿)有效地抵消了矿石品位下降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对于铜、铝等金属,开采成本的下降速度长期快于资源的耗竭速度,导致“经济上的稀缺”并未发生。此外,金属在使用中不会消失,而是从地壳转移到了“社会存量”(In-use Stocks)中。Tilton (2003) 指出,随着工业化进程积累,废钢、废铜等“二次供给”成为重要的市场平抑力量,其供给弹性通常高于原生矿,也限制了原生金属价格的长期上涨空间。
化石能源的不可再生性以及开采复杂度抑制价格下行。化石能源的使用是单向的熵增过程——石油燃烧后变为二氧化碳和热量,永远无法回收复用。与制造业的规模效应不同,采掘业遵循李嘉图级差地租(Ricardian Rent)逻辑:人类总是先开采最容易、成本最低的资源。Cuddington & Jerrett (2008) ,尽管技术在进步,但能源开采的地质复杂度(Geological Complexity)上升速度极快(从陆地自喷井到深海钻井,再到页岩压裂)。技术进步往往只是在抵消地质条件恶化带来的成本上升,而非像制造业那样大幅降低总成本。这导致能源的长期边际成本曲线是平坦甚至略微向上的。此外,石油市场并非完全竞争市场。OPEC等卡特尔组织通过产量管理,人为制造稀缺,使得油价长期维持在边际开采成本之上,这是工业金属(市场化程度较高)所不具备的。
黄金本质上是一种抗通胀的财富贮藏手段。它和工业生产成本或自身矿产供给的关系不大,只取决于人们持有它的意愿。因此长期看它扣除通胀的走势呈现均值回归并不奇怪。
图3:工业金属和农产品指数
数据来源:David Jacks、GMF Research
图4:黄金和能源指数
数据来源:David Jacks、GMF Research
3、大国工业化是超级周期的需求侧推手
我们发现,当一个人口规模巨大且具备一定经济体量的国家步入人均GDP 5000至10000美元(按2024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关键区间时,可能会带来长达数年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
需求冲击是触发商品价格上涨的主导因素(Radetzki, 2007)。人均真实GDP处于5000至10000美元区间(以2024年购买力平价计)时,正值各国工业化进程的关键阶段,此时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扩张以及制造业产能的大规模铺开导致对能源、金属和其他原材料的需求呈现非线性增长。Stuermer(2014)通过长期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制造业产出对矿产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在工业化阶段显著高于成熟经济体,这意味着GDP的边际增长在此阶段会带来远高于比例的商品消费增量。
过去5轮商品周期对应了美国、欧日和中国的工业化。在图5中,我们展示了1850年以来不同时期步入工业化的大国的经济占全球主要国家之比。每条颜色曲线的起始点对应了人均GDP步入5000美金,而结束点对应超过10000美金。可见,20世纪初(1910s)的商品牛市对应着美国(图5紫线)工业化进程的成熟期。大萧条后至1970s的超级商品周期,则由欧洲复兴与日本崛起(图5绿线)驱动。21世纪初的第五轮超级周期,则由中国(图5红线)的快速工业化所主导。
金融需求也是超级周期的可能推手。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标志着全球货币锚的缺失,美元与黄金脱钩引发了长期的信用危机与美元贬值浪潮。 在此背景下,大宗商品迅速从单纯的生产要素转变为全球资产配置中的通胀对冲工具和价值储存手段。Gorton and Rouwenhorst(2006)发现,商品收益率与通胀率呈显著正相关,与股票和债券呈负相关,在通胀环境下提供了有效的投资组合分散化效应。在1970年代的滞胀期,当股票和债券投资者遭受双重打击时,商品期货指数提供了正的实际收益率。黄金价格从1971年的35美元/盎司暴涨至1980年1月的850美元/盎司,十年涨幅超过23倍;白银价格从1971年的1.3美元/盎司飙升至1980年初的近50美元/盎司,涨幅达37倍;铜和铝在1975至1980年期间则分别上涨超过100%和500%。值得注意的是,滞胀时期的实际工业活动实际上是在恶化的,商品价格的上涨完全源于价值储存和防通胀。
图5:主要大国工业化进程
数据来源:David Jacks、GMF Research
4、供给不足起到锦上添花效果
超级周期的起点往往对应局部投资的低点。图6展示了1925年以来,美国采掘业资本存量与社会总资本存量之比。可见采掘业的长期资本开支呈现趋势性下降,且历次超级周期的启动时点——1930年代初、1970年代初以及2000年前后——无一例外地对应着采掘业资本占比的局部最低点。
采掘业供给缺乏弹性的根源在于其项目开发的极长时滞(Time-to-Build)和巨额沉没成本。据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2024)研究,全球矿山从初始勘探到正式投产的平均周期长达15.7年,其中镍矿平均耗时17.5年,铜矿的深层低品位斑岩矿床开发往往超过20年。这种天然的供给刚性(Supply Inelasticity)导致产能释放永远滞后于需求信号。从图6可见,投资的回升往往滞后于价格的回升。
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2000年前后。在经历了大宗商品长达20年的熊市(1980-2000)后,美国采掘业资本存量占比在1999-2001年间降至百年来的绝对历史低点(约30%水平)。这意味着在“中国需求冲击”到来之前,全球资源行业已经历了深度的去产能与去库存,勘探投入严重不足,基础设施老化。面对需求激增,供给端无法在短期内通过增加产量来平抑价格,价格成为调节供需的唯一变量。
图6:采掘业资本存量占比 vs 大宗商品价格
数据来源:David Jacks、GMF Research
5、上涨阶段,多数品种上涨,但涨幅差异巨大。
超级周期的上行阶段大约7成品种会出现上涨。图7展示了每年名义价格上涨品种占比的10年滚动均值。在历次超级周期的上行阶段,该指标均维持70%以上的较高水平,意味着平均每年有超7成的商品种类价格上扬,摆脱了各自独立的供需逻辑,形成了统一的上涨趋势。
但方向的一致性不意味着收益均等化。图8测算了不同品种涨幅的截面标准差(Cross-sectional Standard Deviation),可见当商品价格攀升至每一轮周期顶峰时,其成分品种涨幅的截面标准差也会同步飙升。以第一轮周期(1850-1898年)为例,在1860年代美国内战期间,棉花价格因供应断裂而出现指数级暴涨,但同期煤炭和铁矿石价格虽然上涨,但涨幅相对温和。这表明,不同品种因其供给弹性的差异(如矿产建设周期的长短)及金融属性的强弱,其价格爆发力存在巨大差别。
图7:商品指数 vs 上涨品种占比
数据来源:David Jacks、GMF Research
图8:商品指数 vs 不同品种年涨幅截面标准差
数据来源:David Jacks、GMF Research
五、当前:慎言超级周期
从历史估值维度来看,大宗商品的起跑线已不再处于低位,且内部估值裂口极大。图9展示了截至2025年12月末主要品种真实价格(剔除通胀影响)自1970年以来的历史分位数。黄金、白银、铜等金融属性或电气化属性较强的品种,其真实价格已处于历史90%-100%的极高分位区间。锌、铝也位于60%分位以上。这意味着,这些品种可能已较为充分地计价了当前的宏观不确定性与AI需求预期,缺乏像2000年初那样“遍地便宜货”的估值修复空间。相比之下,棉花、小麦等农产品则处于历史低分位,更多反映了供给过剩和需求疲软的结构性问题。考虑到工业金属长期处于下行趋势,预计市场难以形成类似2003-2011年那种所有板块共振上涨的普惠式行情,高估值品种甚至面临均值回归的风险。
图9:主要大宗商品真实价格自1970年以来的分位数(截至2025.12)
数据来源:David Jacks、GMF Research
第二,全球范围内缺乏可比拟中美历史工业化的超大规模需求驱动力。当前全球经济版图中,尚不存在具备类似潜力的候选者。印度作为唯一人口规模可比的新兴经济体,其工业化路径呈现出明显的"去物质化"特征:受益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主导的发展模式,其单位GDP的金属和能源消耗强度低于中国同期水平,且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长期维持在20%左右,远低于中国工业化高峰期的45%。东南亚和非洲虽有人口红利,但经济总量分散且发展阶段不一,难以形成集中的需求爆发。至于人工智能(AI)驱动的数据中心建设热潮,其对铜、电力等特定商品的边际需求增量虽然相对较大,但在持续性、广度和刚性上均无法与传统工业化相提并论。
第三,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对通胀的容忍度构成了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内生约束机制。 历史上的超级周期往往伴随着高通胀甚至恶性通胀,例如在第四轮超级周期期间,美国CPI年均通胀率一度突破10%。彼时现代央行理论框架仍未建立,全球处于固定汇率时代,央行对通胀的容忍度较高且反应滞后。然而,过去20年,全球主要央行均建立了严肃的通胀目标制(Inflation Targeting)。这意味着,一旦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能源价格出现全面持续性上涨并开始向核心通胀传导,央行将迅速通过紧缩来抑制需求,从而切断商品价格的自我强化循环,2021-2023年的通胀周期即是典型案例。
在三类极端情景下,第六轮商品超级周期存在理论可能性。其一,若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因财政赤字货币化压力或政治干预而丧失独立性,类似1970年代美联储在政治压力下维持过度宽松政策导致通胀失控的情形再度上演,则商品将重新获得"准货币"的抗通胀属性。其二,若全球主要经济体爆发系统性债务危机,引发货币信用体系动荡和通胀预期抬头,投资者可能如19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那样大规模涌入实物资产避险。其三,若地缘政治冲突进一步升级演变为新一轮全球性军备竞赛或战略物资储备竞赛,则可能产生全面超越经济周期的商品需求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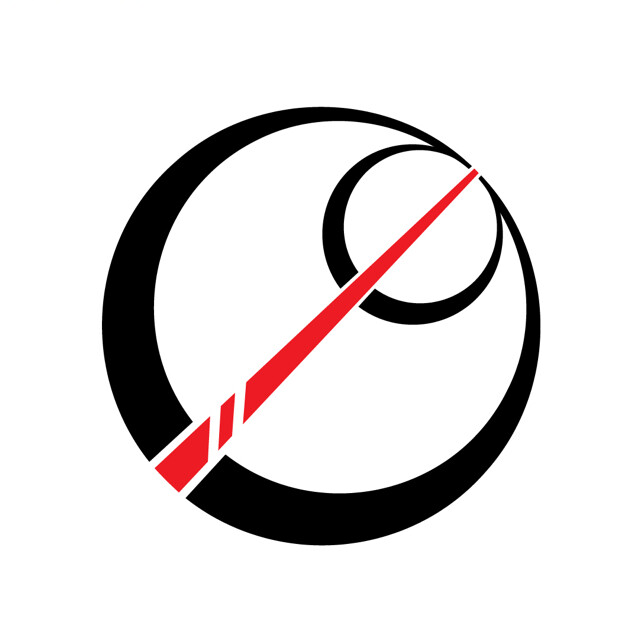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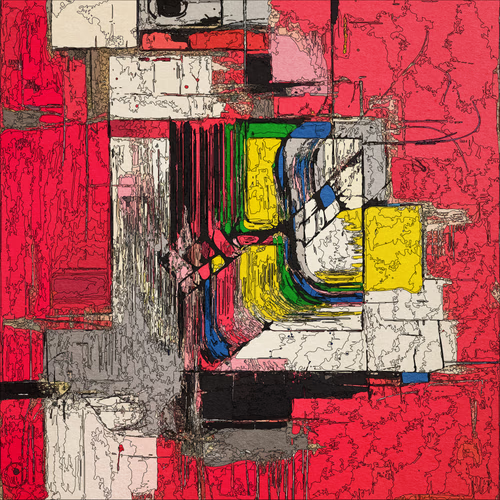














No Comments